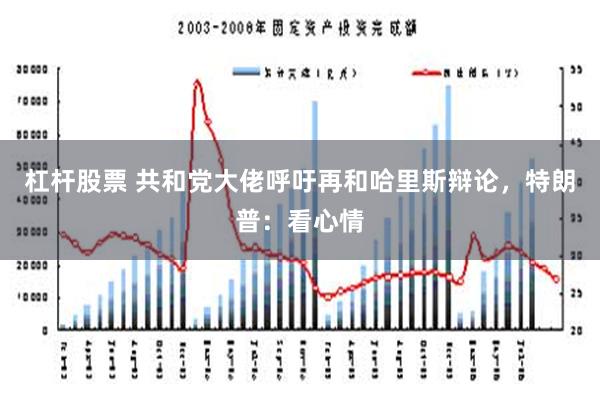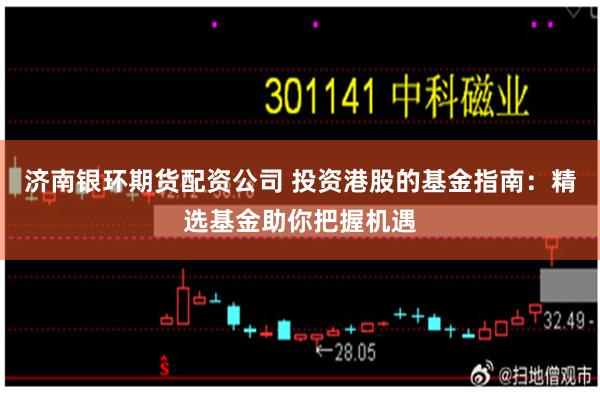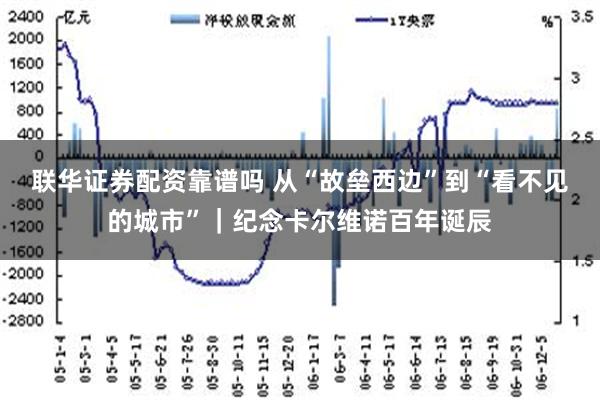
伊塔洛·卡尔维诺(Italo Calvino,1923~1985)停止呼吸后,他的胳膊露在被单外,黝黑,健壮,完全不像一个病逝者的一部分。卡尔维诺的离世,1985年9月19日,是一场天地不仁的掏空,令人睹之心惊,思来震恸。此前5年,他才搬到罗马的这套宅第里,把起居和工作环境完全按心意布置成了植物园。从留下的照片看,所有环绕他的事物都在生长,从工作台,到四处延伸、交织的藤蔓,到书桌上的纸张,到屋里的猫,就连他的身体都保持着生长的态势。然而大脑,那颗众望所归的卡尔维诺的大脑,突然被一阵死风席卷而去。
就像《不存在的骑士》里的设定:全套铠甲齐备,人却不存在了。
他的死因是脑溢血,他最后在写的作品,是即将拿到美国去宣读的“创作谈”《新千年文学备忘录》,写完了预计的八章中的前五章。虽然未竟,但五章内容的“完成度”相当高,所谈主题从“轻”“快”“形象”“精确”一直到“繁复”,所提到的作家作品,第一章上来是希腊神话里的美杜莎和珀修斯故事,第五章结束时,则是他的朋友、法国作家乔治·佩雷克的两部小说《人生拼图版》和《物》,从古老到最新,画出完美的一周。佩雷克1934年生,1982年早逝,卡尔维诺太想向美国读者介绍这位欧洲文学的最新发现——也是可以盖棺定论的发现——他说:佩雷克出版于1978年的《人生拼图版》“重新唤起我们读巴尔扎克所写的那类伟大的长篇系列小说的乐趣”,它足足写了9年,其高度的繁复和谨严,抵达了一个人所可能具备的智性和条理的极致。

词穷
卡尔维诺一直瘦,显得健康。他有一张工作照,一只手的食指触碰打字机按键的时刻,配合他那标志性的“思忖型微笑”,看起来像是好奇的小孩在用脚尖试前方的水。对他这种轻盈的气质产生好感,是很自然的事情,也会自然想到他的各种小说里,尽管情节不一,想法多变,那个轻盈的猎奇味道还真是没有真正变换过,即便他50岁后,头上的白发已经藏不住了。
名作家在50岁上下,往往会写出个人最成熟,通常也最有分量感的小说——纳博科夫在50岁写出《洛丽塔》,托马斯·曼在50岁写出《魔山》,约翰·斯坦贝克在以《愤怒的葡萄》等作品成名已久之后,于1952年拿出了一部他欲留给人类的厚重小说《伊甸之东》。但对卡尔维诺来说,用来为50岁的成熟加上注脚的,是一本小小薄薄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。
它没有真正的“情节”可言。从1960年代开始,卡尔维诺就着力写那些“关于书的书”“关于写作的书”“关于阅读的书”,即触及了阅读、写作、言说这些基本行为的书。《看不见的城市》里,一个想象中的马可·波罗,面对一个想象中的忽必烈汗,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不懂如何交流。“所有的语言都在写作时被压抑”,卡尔维诺说,这里的“写作”是最宽广意义上的,不仅包含书写,也包含言说,包含思考。马可·波罗想要说出真实的见闻,却不知选择什么样的词汇,才能在自己眼前唤出他所见过的景象。于是,沉默,欲言又止,成为言说的开端,那被压抑的语言源于使用它的人对它产生了怀疑:它不过是个符号,它跟我想讲出的东西是一致的吗?
实际上,在1950年代写出“我们的祖先”三部曲时,卡尔维诺的小说就有个特点:对话不多,且很“基本”。很难有什么人物对话,或是独白,或是大段的议论,是我们在看完《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》《树上的男爵》和《不存在的骑士》后能记住的;卡尔维诺心爱的“树上的男爵”柯西莫,一生做了许多事,却没有留下什么话,他永远在做新的事情,即使晚年在树上行动困难,没什么事可做,他也从未向人谈论旧事,“总结”人生;他的死是一个相当经典的画面:朝一只路过的热气球跳去,抓住锚绳,远远地飘往海的那边。记下这件事的叙事人,也即柯西莫的弟弟,对哥哥的一生传奇也没有发任何的感慨。
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也讲出了对话之难,马可·波罗先是打着手势,然后尝试开口,讲完后闭嘴,重回打手势,用来补充言语未能传达的“感觉”。当小说写到这种手势传达时,我们感觉语言仍然是笨拙的,卡尔维诺在此穷追猛打地暴露语言的无能,因为词语不得不被大量地浪费,只为描写短短几秒钟之内的人物动作:
“于是,在以精确的字眼说明了每个城市的基本情况后,他会对每座城市做一番无言的评论,伸出手掌,掌心向前,向后,或向两侧,角度笔直或歪斜,动作或快或慢。他们两人建立了一种新的对话方式,可汗满戴戒指的白皙的双手,以威严的动作回答商人结实、敏捷的双手。”
这段话直让我想起卡尔维诺放在打字机上的双手:他在写作并面对弹动的手指头时,可有哪一刻是没有想到写作是不可能的?
语词在很多时候是更合适的。孔子说过,上古之人“多识于草木鸟兽虫鱼之名”,给事物取了名字,使用和传播这些名字,会使人感到自己在认知世界;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也思考过孩子求知的规律,他说自己最快乐的时光之一,便是在百草园里识万物之名。从无到有地认知世界,可以使人如此沉浸而喜悦。可是,假如一个人有幸成熟起来,并且继续渴望传达所见所思,他就会发现万物的动作,事物的“感觉”,人的“生活”,城市的“气氛”,这些抽象的、脱离于语词的捕捉之外的东西,对自己构成了真正且有意义的挑战。
“至高无上的忽必烈汗啊,”马可·波罗说,“无论我怎样努力,都难以描述出高大碉堡林立的扎伊拉城。我可以告诉你,高低起伏的街道有多少级台阶,拱廊的弧形有多少度,屋顶上铺的是怎样的锌片;但是,这其实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你。”

语词不仅不能言说,而且还必须去言说不可言说之物,因为语词是人的存在之舟,开口说话、阅读和书写时,人方才成为人。弗洛伊德在《释梦》中讲,对梦境做阐释,在本质上不可能达到明确的结论,因为梦是一种“无以名状”的现实,《释梦》因此先开列了一个词汇表,既给出了作者所要确知的工作对象,又为语词表达的知识划定了可掌握的功能边界。卡尔维诺也许受过《释梦》的启发。100多页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,是以书写梦境或回忆的形式来叙事的,它又被划分为一则则小片断,仿佛把语词承担的任务分割到最小,一旦逾出能力的范围,就戛然而止。语词随时一面使出浑身解数,一面袒露其无能为力。
失忆
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人道是,三国周郎赤壁”。苏轼的这几句,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里得到了遥远而有力的呼应。请看“城市与记忆 之四”,这则小片断的开头说:
“在六条河流与三座山脉的那边就是左拉,这是一座你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终生难忘的城市……”
苏轼的词里,“故垒西边”不仅为“虚指”,而且将语词放入一种梦境状态:“西边”本无所谓是哪边,只表示“在那里”,也无所谓发生过什么事,只需“人道是”——人们都这么说,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周郎赤壁是在故事之中的,是通过语词而发生的。而在卡尔维诺笔下,马可·波罗一开口,就知道城市存在于他的语词之中。城市是被说出的,所以,对一个城市留下印象以至于能够言说它的过程,在卡尔维诺或是他的马可·波罗看来,要比说出城市的种种事物、台阶的数量、城墙的高度之类更具意义。这座名叫“左拉”的城市,和苏轼笔下的赤壁一样,都不是被描摹的对象,而是一个“由头”,读者应该由以思考它是如何“发生”的:
“左拉的独到在于能一点一点留在你的记忆中,那些连贯的街巷,街道两边的屋宇,房屋的门窗等等,虽然并不显得特别漂亮或罕见,却都能占据你的记忆……”
“金宵一刻”微信公众号的简介显示,其为“生蚝、生啤、海鲜小酒馆”,主打“源头直供,食材更新鲜”。背后的认证主体为上海金宵一刻供应链有限公司黄浦区第一分公司,注册时间为2024年7月27日。经营范围包括餐饮服务、食品销售、餐饮管理等。
关于左拉城的这一小段,结尾是最使人惊讶、也是最使人恍悟的:此城的存在是因为占据人的记忆:“但是,我要登程走访左拉却是徒劳的”——二元对立在此刻被轰然打破,认知者和认知对象不再分为主动的前者和被动的后者,前者不能像指认一个普通的事物一样,指认后者。于是,左拉仅仅剩下了一个为了言说方便而使用的名字——“左拉”。
“为了让人更容易记住,左拉被迫永远静止不变,于是就萧条了,崩溃了,消失了。大地已经把她忘却了。”
因静止不变而崩溃、消失——世上每一个沦为“景点”的地点,其命运不正是如此吗?
人们可能可以说出《看不见的城市》里讲了哪些古怪的城市:一座建在湖边的城市,游人总是能同时看到城市和湖水中分毫不差的倒影;一座半边永久、半边要拆卸的城市,每年总有那么一天,工人要把宫殿拆散,把水泥柱子推倒,把市政府化整为零,把船坞、医院、炼油厂大卸八块后装上拖车;一座以天文学家为最重要的职业的城市,天文学家们观测天国的秩序,确保它与城市的秩序相吻合……可是,这些城市并非《山海经》里奇肱国、焦侥国、女儿国之类,对它们的叙述,使人明白它们不仅依托于充分的想象,更依托于叙述,叙述建立它们也取消它们,在说出它们的名字时就使它们流动不居。

忽必烈汗从其中受益:马可·波罗的叙述并未让忽必烈汗领略“异国风情”,而是使他看到他对自己的帝国根本就一无所知,那个据说是广袤无比的帝国,因为没有被任何人做如此的讲述,而几乎相当于一个单调的废墟。可汗感觉到了空虚和失落。他不为自己没有去过那些奇异的城市而遗憾,他遗憾的是,自己不曾像对面这个意大利冒险家和商人一样,被关于这些城市的记忆所“占据”,并拥有开口叙述的机会、能力和一定的智慧。
实际上,如果卡尔维诺让他的“祖先”,比如说让《树上的男爵》中的树上人柯西莫得到一个马可·波罗式的机会,能够开口叙述,他们也会这样来表达。卡尔维诺钟情的人物,不一定博闻强记,脑中装下全部的见闻和阅知,却能用叙述来撼动、来搅扰人们一向不曾怀疑其存在的真实。叙述使真实变得不重要了。这就是为什么,推究苏轼去过的赤壁是真赤壁还是假赤壁,是一件极为无聊的事情,或说苏轼借题发挥,阐发“思古之幽情”,但关键在于这幽情是发自苏轼的叙述。
无我
在四五十岁的时候,卡尔维诺想的不是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语词,而是继续摆脱语词的重量。《命运交叉的城堡》往往被视为他在“我们的祖先”后的转型之作,可它实乃后者的自然发展;子爵、男爵和骑士不仅在一定意义上逃脱了常规的生老病死,而且逃脱了确立这一套秩序的话语行为。他们少言寡语,说话也不字斟句酌,是因为卡尔维诺“志不在此”,不想假托想象中的18世纪奇人来发什么警世之言(但不代表他对世界没有严峻的看法)。在《命运交叉的城堡》里,人们通过图像——塔罗牌——在话语之外觅得一条幽径。
马可·波罗用手势来扩展言语的范围,同样,塔罗牌表示出的东西包含了更多隐藏的东西。在图像里,没有一个故事是确切的,它们反证出语言的清晰是一种虚幻。人们想说故事,但一摆开牌,一旦感觉某张牌讲出的故事过多,就会有人把它抢去,用到自己想说的故事里;同样的牌在改变顺序后,说出的是不一样的内容。每一个面对一组牌开口说话的人,用的都是既自信、又揣测性的语言,他会说:“我们同行的人大概是想告诉我们……”“这一列牌一定是要宣称……”——此类语言表述一再地返回到语言表述本身,表明在众多可能的表述里,它仅占其一。

卡尔维诺持续一生所做的事,不只是写作,而且是引导读者思考什么是写作。他自己需要回答的是“为什么写作”。《命运交叉的城堡》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以及“我们的祖先”三部曲,当然还有1979年发表的奇书《如果冬夜,一个旅人》,都是在这一回答的过程中产生的。当然了,俗念总归会爬上读者的心头:人们总要问,为什么他专事想象里的田地,却从来“不写自己”?
在“我们的祖先”三部曲首次结齐的1960年,他为这部书写了一篇序,其中有很深沉的失望之语。他说,与“树上的男爵”柯西莫这样终生任性、自由驰骋、享受孤独的人相比,今天的“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煞了,而且人被缩减为抽象的集合体,他们的行为都是被预定好的”。人们丧失了自我,“不是部分丧失,是全部丧失,荡然无存”。
自我的丧失是个深刻话题,当然不能粗率谈论。但从卡尔维诺少量的“现实主义”小说如《监票人的一天》《房产投机》中,可以看到哪怕在意大利阅读市场极为活跃的五六十年代,他都宁愿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去书写现实。对现实中的话语的巨大的不信任,使他的思考始终及于“全体”而非意大利或是他本人。在越战时期,他说过“越南人民是唯一带来光明的存在”,因为他们是在真实世界里活着的,只有他们能够做到讲述自己独特的真相。在以《看不见的城市》标注出50岁的人生节点之前,他就在一次访谈中说过“我突然感到自己不得不开始我的老年生活……我甚至希望它早点开始”。
少数的文化人之所以出类拔萃,不在于他们的文字和话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世界,而在于他们成功地把同世界的战斗,以及同自然规律的战斗,转化入了智性的领域。典型的例子如盲人博尔赫斯,如远离故土的纳博科夫,如在一场无望的政治事业里孤身坚持的爱德华·W.萨义德。卡尔维诺也可列入其中。《看不见的城市》或《命运交叉的城堡》,都是在“找到一片新的领地、一种新的地理,书写一个可能的故事——一个故事讲述者的故事”(《伊塔洛·卡尔维诺:写小说的人,讲故事的人》作者让-保罗·曼加纳罗语);在《帕洛马尔》中,帕洛马尔先生对符号构成的世界发动攻势,他的整个故事体现为一番智性的情境,如同马可·波罗和忽必烈的对话。
吟咏“大江东去”的苏轼,所做的不也是这样的事?虽然他并无明确的意识,可是“故垒西边人道是”中有着崭新的地理。如果诗受限于必须“言志”,则写词不妨松弛。在1978年一次接受《国家晚报》的访问中,卡尔维诺说他羡慕那些“自给自足”的作家(他举了美国作家亨利·米勒和索尔·贝娄以及瑞士作家马克斯·弗里施为例),对他们而言,只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重要的,“个人经历”就是他们的一切,只需无穷无尽地“写自己”。他很羡慕他们,认为他们没有浪费自己的一分一秒生命,然而他不同:“我觉得别人不会对我的事感兴趣”。我们从《生活在树上》这本传记里可以看到,即便对他的一切都感兴趣的传记作者,也用轻柔如毛掸子一样的笔触书写他,使这颗突逝的大脑所留下的空缺始终保持原样。
举报 文章作者
云也退
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相关阅读 约瑟夫·罗特:一个背井离乡、怀恋故国的世界主义者
约瑟夫·罗特:一个背井离乡、怀恋故国的世界主义者世界在解体,族群在互相敌对或是为利益而结盟,而罗特用写作抵御解体,他一手拿着烈酒酒杯,一手笔走龙蛇,收工之后还不忘在桌上留下可观的小费。
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09-06 16:12 詹姆斯·鲍德温:破解性别和肤色神话的黑人文化明星
詹姆斯·鲍德温:破解性别和肤色神话的黑人文化明星鲍德温是美国的文化明星,在上世纪黑人文化的全明星阵容里,他占据一个无可争议的位置。
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08-16 08:57 还原一个被焦虑、不自信缠绕的卡夫卡
还原一个被焦虑、不自信缠绕的卡夫卡谈论他成为一个符号,一个被消费的名字,一种能寄托许多情感的象征物,也是最常见的、很能显示作者阅历的缅怀卡夫卡的方式。
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07-19 09:18 艾丽丝·门罗去世:她在世界一隅,慢慢挖出生活的奥秘
艾丽丝·门罗去世:她在世界一隅,慢慢挖出生活的奥秘当地时间5月13日晚,加拿大著名作家、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·门罗(Alice Munro)于安大略省逝世,享年92岁。
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05-15 17:03 生活对他开的每一个荒诞玩笑,他都给出了更荒诞的回应
生活对他开的每一个荒诞玩笑,他都给出了更荒诞的回应当赫拉巴尔在废品站干满了5年联华证券配资靠谱吗,将两只被化学药品伤害过的手再次放到打字机上的时候,他真正感觉到自己坐到了一个荒诞世界的正中心。
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05-09 22:42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,不代表证券配资利率_证券配资工具_证券交易系统观点